李佩甫:河南许昌小说家,代表作生命册获茅盾文学奖,作品译介至多国
李佩孚,小说家; 1953年出生,河南许昌人;中国作家协会常委、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着有小说《生命之书》、《羊之门》、《城市之光》、《城市白皮书》、《等等》11部。以及“李家”等11个单位; 《钢铁婚礼》、《田园》、《李佩孚集》等7部; 《英和故事》、《太平洋故事》等电视剧6部;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出版奖等;电视剧曾荣获飞天奖、华表奖。等待。
我写一个

特定区域的精神生态
○
李佩芙/烈西峰
“平淡”是我的精神家园
西风:
李老师,您能谈谈您最近的小说吗?
李佩孚:
我的部长小说两年多写了两年,但准备时间却长达十年。表面上看,这应该是一个“反腐”主题。我写了杀害平原副都督妻子的案子。其实我写的是一个特定领域的精神生态,也可以说是一封“民众批判信”。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 30年来,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火车高速前行,在大家“失重”的巨大变化中,目标已经迷失在眼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烂是从底层开始的,可以说是全国性的。于是,我就从“花客”开始了(说白了,“客”是一种尊重,门外的人流就叫“客”。但这里所说的“花客”名义上是协调花卉交易的中间人) ,但实际上是客人。)这篇部长文章的全部内容都是由这样一位“花客”引起的。一个卖“花”的人从小镇的花市开始,引发了一系列的人和故事……于是,这篇部长文章的名字就叫:《平原》。
西风:
你小说的主题常常涉及“权力”和“人心”。这本小说延续了这个主题吗?和你以前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李佩孚:
应该说,也可以说不是。从表面上看,“权力”是社会的外在形态,书写当代生活离不开权力。然而,“人心”是固有的,是变化的,与时间和历史有很大关系。我说我把“人”写成了“植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羊门》写的是“草”,写的是原生态。主要写在特定时期,“土壤”与当地“植物”的生长和关系。就这部小说而言,它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城市”的出现和“城市”的诱惑。写“逃”,就是对“光”的追逐。 《生命册》第三部分写“树”,以树来比喻。写50年的历史,写“树”的成长现状和背景。同时,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50年的内心独白。是这片土地的回归,也是对距离的重新认识。它写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植物”(人)最好的部分上。这些“花”有光彩和绚丽,有“花”的“轨迹”和“变化”,有在时间和档次中书写这些“植物”的过程。我想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与“土地”同行的人。这不是一个沉重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不能扔掉的问题。例如,“伤口”;一条“尾巴”,或者说是“胎记”,它生长在身体上,蕴含在血液中,不断被切割。你只是在“触摸”、询问、回头看。一个行走的国家迫切需要制定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规则。

文学时间是心理时间
西风:
有人评论说,你的写作几乎都是从中原文化、城乡、历史与现实的互通出发,写那些失败甚至毁掉的信仰和残余信仰。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李佩孚:
“平淡”是有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是我的写作领地。有一段时间,我的写作方向一直集中在“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写了“成长”。也可以说写的是“平原”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在特定区域,时间上,气候、土壤、河流等生态环境对一花一草一木的影响。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从“根”来说,中华文明对中原大地的渗透最为深入。然而,五千年文明史也如五千年锁链,精华与糟粕并存,血液中的毒液与乳汁混合在一起,就像现实生活中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一样。我想说的是,我们正在长大,但我们每天都在喝这样的牛奶。
西风:
您是否曾对中原大地、人心进行过深入剖析。你能说你的小说是《中国农村病人的报告》吗?
李佩孚:
我写的是“平淡”。这平原不再是某处,而是我心中的“平原”。我对平凡人有一个概括:勤劳、努力、求生、生活、生生不息。
西风:
您的工作一直在分析中国当代农民的精神。你能总结一下吗?您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洞察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和我们的灵魂状态?
李佩孚:
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精神疾病高发期。当我们吃饱饭的时候,我们又面临新的“生态危机”。这辆因施工而得名的高速列车已无法刹车。我们不知道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人类如何与自然融合,这是一个民族的新命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从虚拟的天空回到大地时,大地已经布满了目光,我们已经失去了诗意的“家”。是的,这一切离我们都很近。看到危险,但我们没有敌人。也许,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西风:
你的小说跨度很大,《羊门》有四十年,《生命之书》有五十年。你如何理解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你擅长讲故事,你如何理解小说的“故事”?
李佩孚: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时间是心理时间、感情时间。它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引用的,并以浓缩、凝练的文本形式表达出来的。它穿越了时间的迷雾,表达了沉峰对生活的深刻认知。这也是一个抢救的过程。对这片土地没有深刻的理解和热爱是无法挽救的。说实话,我并不太在乎所谓的“故事”。我关心的是表达和塑造人物。如何准确地表达社会生活和人物形象。有时候,必须把角色推到极致,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故事就出现了。故事的发展是随着人物的命运而展开的。

我把“人”写成了“植物”
西风:
小说《羊门》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当年曾引起争议。我想知道你创作的初衷。 《羊门》的寓言性相当强。一位村支书40年来构建了从乡镇到县城、从省城到京城的庞大关系网络,不断将村里的人才输出到城市,从而让村里一步一个脚印。这个人物的造型非常生动,但也让读者感到不可思议。
李佩孚: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城市小工人家庭,家里的亲戚都是农民。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的家里度过的。小时候,我曾光着脚,光着脚跟乡下的孩子们一起割草。到时候,六年的草就可以干活了。同时,我的母亲是一个好客的人,所以农村的亲戚经常来我家吃饭。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祖国的一位亲戚来到我家,我手里拿着一串串的蚂蚱,上面还串着一串毛茸茸的草。 (知青),后来当上了生产队长。虽然我出生在工人家庭,但我和村民们还是有很多联系的。自专业创建以来,我还当过副县长。更重要的是,当我把“平原”作为我的创作源泉时,我每年都会走遍平原上的几个县,不是为了寻找素材,而是为了熟悉这里的变化……于是我认识了乡村等干部。 、平原,还有很多村的村支书。 《羊门》里的村支书,集中在我从平原学到的几百个村支书。他是平原上全体村干部的集中体现。因为他是一个被塑造和集中的人物,所以他并不孤单。他是一个代表。农村里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
西风:
有评论称,《羊之门》通过描绘乡村权力运作、展现各级官场的斗争,塑造了一个“中原之国”,塑造了一位“东方乡村教父”。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李佩孚:
我说我把“人”写成了“植物”。在这片土地上,最好的植物(人)能生长成什么样子。我只是写下了这片土地上的各种生命形态和生存方法。
西风:
《羊门》开场不久,您就分析了中原“气骨”文化的成因——“从民间传说来看,这是一片无骨的平原,一片羊场,翻开了历史”书上说,你从根本上来说,人是站不住的,因为没有山,没有水,就没有支撑。”
李佩孚:
我见过很多县。平原上,这里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说明早年间,这里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这片土地是一片平川,四季分明,平均气温16.8度。可以说,木棍是可以发芽的。同时,这里无山无水。人出来了,一个头就撑不起天,更谈不上“活”了。所以,这里的人首先要建造一座“房子”来隐藏自己。当时有一个词叫:朝鲁中原。一旦有人打斗,这里就没有危险了。故有“得天下者”之说。所以,这里又是一个杀气很大的地方。历代战争,犹如割草。战争期间,由于当年发生的天灾和人祸,这里的生活十分低落。因为杀气重重,砍了又一把茬后,就有了“败生,求生,生生不息”。
西风:
何波对“场”的手术是手术。他像勤劳的农民一样“播种”了几十年的力量。最终在省、市、县三级干部中建立起了庞大的“人才库”。如此一来,就可以在中央层面形成一个“老干部网络”,就像魔幻现实主义一样。你怎么相信的?许多官场小说,尤其是“反腐小说”成为一种潮流,而您却被视为描写中国“官场”最深刻、最强的作家。你自己的经验或者官场从哪里来的?
李佩孚:

客观地说,我对官场并不是特别熟悉。我熟悉“平原”和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当然,作为一个作家,我每年都会下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行走在平原上,我常常会“捡起”一些东西,这就是我注重的“细节”。捡到这些“细节”后,我就储存在脑子里,等待有一天发酵,及时发酵。所以,我在一个特定的区域生活了很长时间,也有了一些认识。我始终认为,认识大于生活,理解生活。
西风:
从你的《羊门》、《城灯》到《等待灵魂》、《生命书》,无论是“门”与“灯”,“灵魂”与“生命”,你关注重大主题,但这些主题都与“人”相关,即你通过关注人来关注社会的其他问题。
李佩孚:
正确的。我一直关心着平原上的人们。他们是我的父亲和同胞。我在平原长大,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与我息息相关。有时候,日子很“痛苦”,我也感受到了这种“痛苦”。
西风:
你为灵魂部长准备了长达20年的时间。这位部长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一般作家难以做到的。人很厉害,这些材料怎么得到呢? “金阳光”奇迹般崛起,成为全国领先的超市运营商,但种种诱惑却让人失去灵魂,最终崩溃,一切都如同一场梦境泡沫。这是对现实的批判和象征吗?
李佩孚:
我在省城生活了30多年。郑州可以说是中国的十字路口,交通发达。在这样一个相对落后、一直跟风、商业氛围缓慢、容易走极端的城市里,我花了20年的时间,关注一个比较大的商业集团的发展和消亡过程。尤其是公司的董事长,曾经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他在中国受到了影响,后来逃到了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人给了我很多启发。当然,为了了解业务流程,我也多次来到商场,跟随人们在柜台前闻各种香水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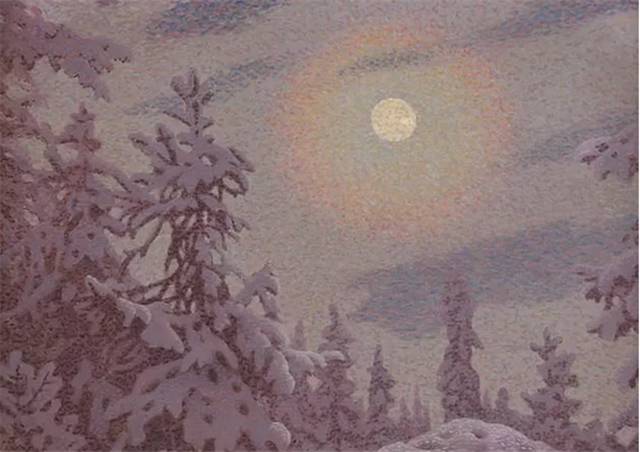
我不太关心“教义”
西风:
你如何理解现实主义?您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吗?
李佩孚:
说实话,我不太关心“主义”。我不在乎它是“现实主义”还是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还是其他什么。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读过世界各国流行的各种文学主张所产生的文学作品。我已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了。我认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领地”。我的领地是“平原”。有一个参考部门。我想这也是一种种植吧。我厂有“声”,声来自平原。也可以说是特定区域的声音。无论声音叫什么,无论声音大小,我只要求它是独一无二的。
西风:
为了能够进城,农村青年冯家昌压抑人性,迷失自我。事实上,我们在作品中很注重人性。你在工作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李佩孚:
《城里的灯笼》是我的第二本平原二部长篇小说,主要写《逃亡》。写出对“光”的追逐和向往。在当年的户籍制度下,农村孩子要想改变命运,进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上大学,二是当兵。小说中,农村青年冯家昌通过军人的通道,一步步从农村走向城市。事实上,他的抑郁症并不是从城市开始的,“原因”早在童年就种下了。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了他的一生。早在童年时,当他的脚踩在稗子上时,他就知道“天痛”。
西风:
小说《生命之书》反映了五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但你关注的是“我”,即吴志鹏作为生命个体的心理变化。请谈谈你对这个人物的设定和塑造的想法”精髓《生命之书》采用树状结构,各种颜色的人物等都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这会不会损害小说的真实感?
李佩孚:
《生命书》这本书,我写了一个“与土地同行的人”。主要写“土壤”或“背景”。本书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我”的“生活背景”。这部作品通过一个“嫩芽”的生长过程来展现“背景”和“土壤”。这里我们要告诉人们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滋养它生命的“营养液”是什么?同时写出“我”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为一棵树。 “我”怎么就成了流浪者,成了无根的“树”呢?我在写《生命之书》时遇到了三个困难。一是时间跨度大,写了五十年;二是结构难度大。我以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切入,这在建筑意义上是困难的;三是语言难度。独特的、基于文本的用词方式。首先,过去50年,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要写的东西太多了。我的生命储备已经用得差不多了。长篇故事采用第一人称,有一定的局限性。过滤生活、切割内容非常麻烦。特别是在结构方法上,我用的树状结构,我用“气”来做“骨”。不过,吴志鹏内心的想法却是活跃的。从风尘中,有枝条,有顽固,无法散去。这也是费了不少心思。对此,我尝试用一些“暗笔”,比如“见字如面”,比如“吃牛奶”,比如这位部长的“钥匙”。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语言。我一直认为,文学语言不是语言本身,而是思维和认知方法的表达。
西风:
《羊门》小说的最后一幕令人震惊。因为胡波的遗愿就是听听狗的惨叫声,村里的狗在一场杀狗运动中被杀死。这个结局非常具有象征意义。请谈谈写这个结局的初衷。
李佩孚:
写《羊门》小说有两个难点。一开始我写得很顺利,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第一个困难是名字。小说写的时候,名字还没有想好。可以说,这个名字的名字就充满了悲伤。后来晚上,我半夜睡不着,就起来翻书,就把别人送的一本圣经放在枕头边,看着。于是我看到了几个字:我是门,我是羊的门,大家都是从我这里进来的……于是我终于有了书名。第二个困难是结局。小说写到最后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俗话说:篮子里的篮子重在收藏。但我管不住“嘴”。我曾经写过八个结局,但我并不满意。为了这个目的,我拖了一个多月。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最后,我终于想到了这个结局。虽然有点短,但当“狗”叫的时候,“尾巴”终于甩了。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痛苦
西风:
你的写作习惯是什么?在家写作,还是远离家人和朋友?
李佩孚:
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全部的时间。我主要是业余写的,都是躲着写。从事专业创作后,我在家写作。那时候我最怕见面,尤其是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后来我发现人是有生物钟的。人的体能和智力受生物钟支配。我慢慢地发现了书面的法律。在我的一天中,最好的写作时间是早上。一年中,最好的写作时间是夏天,越热心就越活跃。秋季和冬季次之。
西风:
你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李佩孚: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我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整天在水泥台上打。后来我喜欢上了打篮球,早上4点30就起床了。我真的很想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为此,我还挖了坑练习弹跳……中学时,我还曾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打完排球后,我的手指弯曲了。后来,当我在农村当知青时,县体校篮球队招募了战士,运动的教练给了我特殊的措施。人家要求一米八高,我却只有一米七八两厘米的距离。很遗憾。后来我把它写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就很少玩了。
西风:
能谈谈你的首秀吗?写作和出版是否顺利?
李佩孚:
我的处女叫《青年建设者》,发表于1978年《河南文艺》第1期。当时我还在工厂。 1977年春天,我第一次接到《河南文艺》的通知,要我来省城改稿。那时,我很高兴。我想既然通知我进省城改稿,就必须要用。来了。但到了郑州,听完编辑的修改意见后,我傻眼了。他说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好像是被重写了。于是我日日夜夜地结束了。八天内我改变了八次。越改变越失望。最后编辑告诉我: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编辑说你可以改什么。我无法改变,所以我逃走了,随身携带的东西也被遗忘在招待所里。在火车上,我还看了一眼郑州恨!回来后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后来发表的《青年建造者》。
西风:
有人说你是一个“苦练”的作家?能谈谈你辛苦工作中的乐趣吗?写作中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李佩孚:
年轻的时候,我确实很努力地写作。我感觉就像“盲人骑盲马”。当时我找不到写作的方向。这个阶段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后来就好多了。当我有了写作的方向,有了自己的写作领地后,情况就大大好转了。写作的时候有苦,当然也有快乐。当找到最准确的表达方式,想到一个好的细节时,就有一种“指甲开花”的快感。
西风:
你的工作重点是精神的引导。您好像说过,当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思维语言指南时,是非常痛苦的。你能谈谈这种痛苦吗?
李佩孚:
是的,我在某个场合说过这样的话。我当时谈到了“文字”。我认为一切都是有用的。任何无用的东西都是无价的。比如一把椅子,怕是金子做的,可以从材质和工艺上算出它的价格。但有些东西,它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比如百米赛跑九秒,足球比赛就打进了好球。比如梵高的油画等等,你很难计算它的价格,因为它对现实生活没有用处。同时也体现了人类体能、智力和想象力的极限。所以它是无价的。文学应该属于这一类。它要有尺子,体现主导民族语言,还应该有“光”。尤其是在“文本”的意义上,中国文学还存在着距离。我所说的“文本”,并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文体形式,是文学语言行走的方向,是一种独特的创造力。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痛苦,因为每次都要重新开始。
西风:
你能谈谈你的父母吗?
李佩孚:

我来自一个工人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国营工厂的工人,也可以说是一名鞋匠。十二岁进城当学徒。他做鞋已有四十八年了。他六十岁退休,后来去世。父亲是一位优秀的鞋匠。父亲生病之前,我给我做了一双棉鞋。二十多年来,我仍然把它放在鞋柜里,每年都会拿出来几天。我刚刚写作三十多年,与父亲有距离。我的母亲也是国营鞋厂的一名工人。三年天灾被下放,成为家庭主妇。我们一家五口,她的兄弟姐妹中,她对我们家的贡献更大,她是我们家里最勤劳、最有能力的人。她愿意做任何事情……但她的母亲后来去世了。
西风:
你童年最难忘的是什么?
李佩孚:
一是饥饿,二是“饥饿”。第一种饥饿是吃不下肚子;第二个“饥饿”是我到处借书,却找不到书看。
西风:
你好像说过读书拯救了你。
李佩孚:
我的父母不识字。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是我们家里最有文化的人。那时,我们家能找到一个有文字的东西,那就是半黄历。所以,凡是有文字的东西都是极为罕见的。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有一本书。这本书被他父亲锁在柜子里了。他每次都会偷走它,让我看看他用的是什么,比如一块糖或橡胶之类的。他还是有限制的。一本最多头的书,限我三天,所以很痛苦……后来又借了旧一点的书。精华 县图书馆、市图书馆、地区图书馆、工人文化馆图书馆。我看着它,我能找到的一切,一切都可以看到。最早的单词无法识别,出现了问题。多年后,我已经明白了那个词的意思,但我会读错音,中学时被同学称为“白字先生”。
西风:
你觉得读书怎么样?有哪些习惯?你一般看哪些书?
李佩孚:
我认为人的一生唯一的捷径就是读书。这本书是什么?它是人类生命的沙盘,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如果你想生活得更好,或者提高生活质量,唯一的方法就是读书。读书不是为了改变命运,但读书可以更好、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充实自己,净化自己。
西风:
请回想一下你的知青,给你带来了什么?
李佩孚:
我在农村生活了四年半了。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我是一个新的制作组团队。每天和知青一起干活,几乎每天都满头大汗。可以说是很苦了。我最多吃了七个包子。我们队只有四个非常辛苦的劳力,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作为一名生产队长,我经常跟着村干部到乡政府见面,逐渐接触到了很多乡村处级干部和各类农民……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西风:
你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只是知青时期,你一直待在农村,却在农村写下了三分球。你怎么做?
李佩孚:
我说,懂得大于生命,点亮生命。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说,他的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他也当了一辈子农民。他应该是最有生命的,但是为什么他写不出来呢?这就是理解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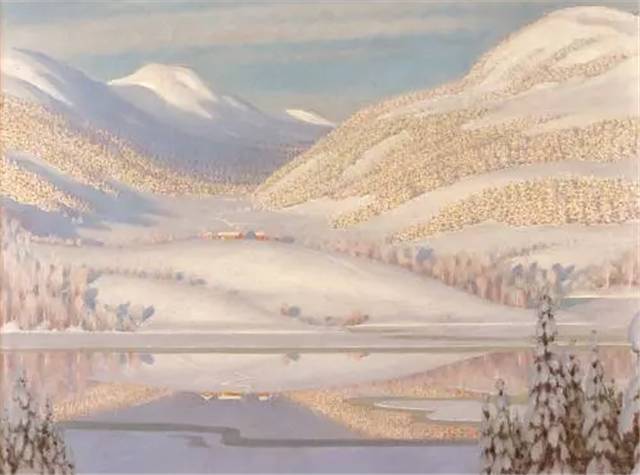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应该说是“文学时代”
西风:
你的小说语言很有讲究,请谈谈你对小说语言的理解和把握。
李佩孚:
文学语言不是文本本身,它与一个人的思维角度和思维方向有着巨大的关系。同一件事是一样的,站立的角度不同,看问题的方式也不同。文学语言反映了作家的认知方向和思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就是思维。它代表了一个人的认知水平,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形象思维能力。
西风:
我曾经看过你在80年代创作的小说《红水瓶与绿水瓶》。在那部小说中,你是否能说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即一个属于自己的“平原”交集?
李佩孚:
20世纪8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些作品。但目前还处于盲目写作阶段。没有找到写作的方向。我到处找资料,写得很卖力。到了1985年,我突然发现我最熟悉的还是我的家乡,于是就有了《红水瓶和绿水瓶》。这部作品后来被《小说月刊》、《小说选》、《新华文摘》转载,成为我的著名代表作。由此,我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向。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它扩大了,面积也很大了。有了平淡,我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领地。因此,作家必须把人物放在最熟悉的环境下写,这样就可以控制出处。
西风:
《羊之门》、《城市之光》、《生命之书》三部曲中,你最喜欢哪一部?
李佩孚:
应该说是《生命之书》。这是我准备时间最长的一次。可以说,我粉碎了我一生中的所有储备。此外,我开始写这位部长直到50岁。经过多年的洗礼,我的心态相对和平,不耐烦。
西风:
许多作家,包括Mo Yan,都认为1980年代是中国作家的黄金时代。你同意?在文学方面,它带给您什么?
Li Peifu:
对我来说,对于1950年代的作家来说,应该说是1980年代的“文学时代”,或“打开所有毛孔,以吸收各种文学营养”。当时,文学的“国家大门”已经开放,各种文学趋势和学说流入了中国。世界各个国家的各种杰出文学作品也被转化为中国。看一本好书是一本好书。文学解冻后的爆发也是爆发。例如,“百年孤独”影响了中国作家多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作家也可以以这种方式写作。
西风:
小说《生命之书》一开始就开了一年。这是一个夸张的声明吗?
Li Peifu:
当第一次写“生命书”时,我没有找到这位部长的语言。我觉得准备时间很漫长而写了。一开始,写了80,000个单词,废除了写作,然后写了。后来,我无法写作,所以我停止写作。在这方面,我去了乡村几个月,然后吃了几盒瞬间面条。这不是要走的材料。我去感受的感觉。我会发现我理解的声音,浅色,颜色和味道。添加一种新的感觉,以免重复。回来后,我再次坐下,搬出了研究,换了一个房间……所以我找到了笔的第一句话,这与我的工作的情感趋势有关。这句话是:“我是种子……”这确实是开始。
西风:
最后,您想让您谈论未来的创意计划吗?
Li Peifu:
四十年过去了,对我来说,写作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方式。我仍然必须写它。我要耕种的土地仍然是“平淡的”,不会改变。
发表于201709年的“年轻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