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礼物:人生必修课教你如何获得内心真正的自由与快乐(语音直播)
人生必修课:
如何获得内心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注:现场语音直播)
(长按识别下图中的二维码联系客服让他帮你团购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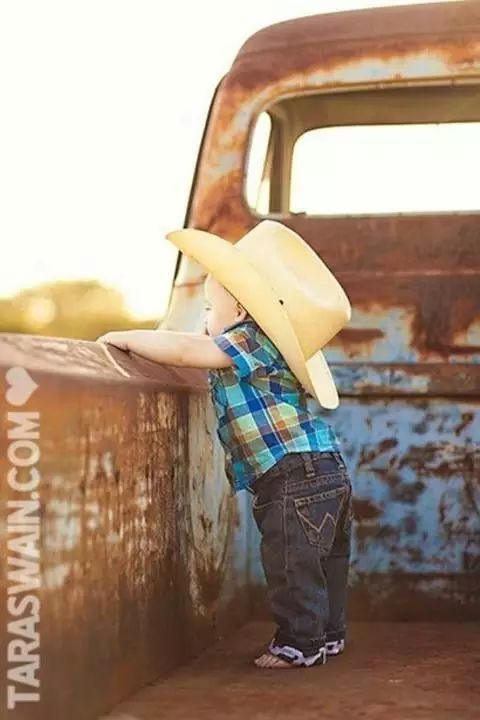
刚开始做记者时,《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曾说过,去现场采访时,“你应该像外国人一样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视而不见。
我以为我听懂了,但当我读到一篇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时,我意识到我已经失去了多少现实感。
他写道:“任静正要出去上班,她妈妈有点慌了,把女儿追到厂门口,求她留下来,说她太小。女孩什么也没说,也没有看她一眼。”女人突然哭了起来,但女孩最终还是屈服了,喊道:“走吧,你想走就走吧。”
她转身慢慢地穿过街道,放声大哭。
一走开,女孩就忍不住哭了,把头埋在膝盖间抽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母女俩站在街道两侧哭泣。两人都很生气,不说话,也不看对方,但母亲还是不肯走。
我姐姐来了,她给马路对面的姐姐发了一条信息:“她告诉你要小心。”
十六岁的女孩回答道:“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
五分钟后,姐姐说:“她在哭。她真的很想让你留下来。”
女孩很严厉地说:“我今晚一到就给她打电话。”
工人们把车装上车。她终于爬了起来。最后,妈妈见她的乞讨无果,就给我寄来了两百块钱。当我站在那里看着汽车消失时,泪水从脸上流下来。
车上还有另外一对姐妹,来送行的是她们的父亲。没有拥抱或悲伤。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衣服要保暖,天气冷,一不小心就会生病,生病了就得花钱。”买药,穿暖和点,好吗?”说完,转身就走。”
中国的古村落就在这个细节上挣扎,头也不回地消失了。

何伟于20世纪90年代来到中国。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静静地看着这里乡村发生的事情而不成为关注的焦点有多困难?但看看他在清明节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
“早上杏花飘落满地,像一场春天的暴风雪……几个人在土坟前走来走去,‘我的祖父就埋在这里。’”
'决不'
“我想是的”
“废话,那是你爸爸的大哥”
何伟写道,“他们很少提及人的名字,只提及与某人的关系,并没有相关细节或具体记忆。”
其中一座坟墓是新的,属于一位两年前刚搬到城里的老人。坟上的新土堆得很高。何伟拿起铲子,在土堆上填了一点土。 ”有人拿起一叠硬币点燃,另一个人拿了一根香烟,贴在坟墓上,香烟竖立着。几个人后退了一步,看着坟墓,议论纷纷。
“他根本没抽过红李子。”
“是的,很贵。他以前抽过黑混蛋。”
“你现在买不到了,它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很流行。”
这是有关死者的唯一细节。站了一会儿,魏说:“好,我们走吧。”
其中一人回头一看:“烟还好吗?”
“没关系”
几人“沿着曲折的小路,下到山沟里,地上有杏花花瓣,扩音器里播放着一年一度的禁上坟、禁烧纸的通知,一行人回到田里开始干活”。

这个美国人,拿着一把沾满泥土的铲子,看到了一个我熟悉的中国。
何伟在美国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学里谈论中国,并让孩子们提问。孩子们问:“中国父母会杀害女婴吗?” “中国人吃狗吗?”他感觉很糟糕。 “为什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
他在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在涪陵教书的时候,课本上介绍美国宗教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学校的介绍是发生过什么样的谋杀案。他向学生们解释道,“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但并不代表真实的美国社会。”
他希望人们在描述一个国家时,应该把背景解释清楚,并利用时间进行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地告诉他们什么是最坏的和最好的”。
他所描述的中国是具体而细致的。
他写了一个名叫魏的农民的家庭。这个偏远的村庄从2003年开始接待更多的游客生意,魏某从务农转行经商后,收入超过3万元,比上一年增加了50%,但一家人却变得焦急起来。
以前男人只是偶尔抽红梅烟,现在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晚上还喝酒,问他怎么了。他说:“我随时随地都会感到紧张。”
他总是担心钱的问题。他花了三十多元买了一双“意大利”牌皮鞋。鞋盒放在很显眼的位置,他还有一件人造皮夹克,这是他离开村子去县城时穿的。优越的。 “中华香烟”效果很好,可以帮助他获得生意。
该男子入党后,社交活动较多。吃完晚饭后,女子给男子打电话,其他人接了电话。她听了一会儿,突然不耐烦了,“他喝醉了是吗?那他今晚会回来吗?让他给我打电话。”
她坐在餐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孩子似乎没有看到她。
然后电话响了,她走到另一个房间去接电话。 “今晚你必须回来。”她的声音很严厉。 “听到了吗?今晚你必须回来。”
何伟出去的时候,发现男人回来了,喝醉了,倒在了墙上。
女性也想像男性一样尝试自我发展。她把自己做的玉米面送到城里去卖,挨家挨户卖,但她不抽烟、不喝酒。她没有“关系”,不得不退到这种孤独之中。在村庄里。
后来,她的口头禅变成了“我无法控制它”。对于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她不肯听,也不听,用这种冷漠的态度来消极抵抗。但人心不能忍受一无所有,所以她信了佛教,因为她听到城市里旅行的人总是谈论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他们对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有自己的看法。”她靠墙摆了两张桌子,上面铺着黄丝布,上面放着两尊佛像、三个橘子、五个苹果和三杯白酒。她感觉平静了一些。
几米开外的白酒坛子里,她的丈夫正在泡刚宰杀的小野猪。
男人瞧不起妻子向上帝和佛陀的祈祷。他是村里唯一读过三十多本法律书籍的人。他要竞选村支部书记,竞选是秘密进行的,双方都没有出手。秘书是个女同性恋,邀请他吃饭。他没有说清楚,但大家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你们不打,等我下台了,就是你们的了。”但他并不打算退出。他觉得书记征地让村民不满意,自己胜算还是很大的。选举前,镇领导开会。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只是表扬了现任书记,然后请他向党员表明立场。他清楚地知道轮到自己了,于是说了句“干得好”就坐下了。
他的政治经历失败了。一位算命师告诉他:“你永远不应该参与政治。”此后,他找到了一个开眼的人,重新装修了天井。这是他学到的另一个教训。 “他再也不会对算命师的警告充耳不闻了。”
这是何伟写的。他说,“西方报纸总是关注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事情,但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是极其个人化和内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索,他们都在运用自己过去的经验”面对现代的挑战,他们有麻烦,父母和孩子处于不同的世界,婚姻也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真正的人在一起,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幸福的夫妻几乎不可能保持脚踏实地。”

何伟不是记者,也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 1996年,他从牛津大学毕业,乘火车周游各地。他路过北京,本来打算停留一周,但因为这里的人“比较”而决定留下来。热闹”。
他从未学过中文,也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 “因为我以前从未研究过中国,所以我对这里的人和事没有任何强烈的态度或看法。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并不是一件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 “如果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中国有所了解,那么到 1996 年就已经过时了——中国已经成为另一个国家。”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可以在中国漫游。租车的外国人不准离开北京,但他已经学会了违反规定。如果发生车祸,租车人会拿出一张“美中拖拉机协会”的证明。空白的介绍信会计入他的单位。
他不能在车里带GPS,因为他担心自己在西方测绘会被视为外国人。他住在小旅馆有时会被报警,所以他晚上就住在土路上。当半夜帐篷里突然亮起来的时候,他猛地坐起来,以为是汽车驶近的灯光,拉开门帘,才发现是一轮圆月从地平线升起。他“静静地坐在月光下,等待我的恐惧平静下来”。
后来,我住在长城脚下的一个偏远村庄,租住在韦家。墙上贴着《还珠格格》的海报和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肖像。 “生双胞胎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据说这是合法生两个孩子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即使是这张照片中的双胞胎也不是真品,只是其中一个的复印件,颠倒过来放在一起。 “厕所里的两块石板之间有一个小缝隙,晚上他就听见老鼠在墙上跑的声音。”每当月圆之夜,这些家伙就特别活跃,这样的夜晚我都能听到他们滚核桃的声音。到屋顶上的秘密仓库来隐藏它们。”
由于他在三岔村租房,村里一个名叫“Shit Trouble”的男子向JC举报了他。他知道“JC只是不想惹上麻烦”。他了解了法律规定,主动上门拜访JC。中秋节送月饼,春节送水果。终于有一天,JC对着搅屎棍说:“别再白费力气了。”
他本来不想写这个村庄。只是生命在人们身上流动。起初只是涓涓细流,后来泛滥成河,蜿蜒曲折。他忍不住观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个精瘦的农村男孩,精力无穷。他喜欢和他一起玩,并称他为“魔鬼叔叔”。孩子们上学后,学校里没有零食,吃的也不多。但回到家,都是进城旅游的人带来的方便面和薯片。每天做完作业,他们就吃垃圾食品,看电视,但妈妈却不这么认为。怎么样,对于农村人来说,“孩子能吃饱是好事,不看电视就浪费了”。
孩子的肚子已经有点圆了,腿上也长了肥肉,跑了几步就上气不接下气了。何伟希望自己能多吃水果,但妈妈却说冬天不吃水果“不利”。她看着儿子,颇为满意:“现在有点像城里孩子了。”
何伟写道,“他们同时过着现代和传统的生活,但他们同时捕捉到了两种生活中最糟糕的部分。我不反对进步。我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渴望摆脱贫困,我也对此感兴趣。”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本书的主题明确如刀,就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然而,何伟并不是从写一部“史诗”的野心开始的。这只是他在人生大潮落下后暴露出来的一个主题。
他的书被称为“非小说类”写作的典范,但他不喜欢被归类。 “我还认为‘非小说’是一个很奇怪的词。它没有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而是说它是什么。”它是“不是某事”。我觉得分类并不重要,即使我的书被分类为旅游书,它仍然有自己的特色。”
在成为《纽约客》的作者之前,他曾长期默默无闻地写作。他从来没有学过新闻专业,也没有被束缚的荆棘。 “我的写作领域是由我个人的兴趣决定的,而不是由出版商或编辑决定的。我愿意真正掌控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种独立性使他更像是一名作家,而不是一名记者。有时,编辑请他报道某个热点事件,他说的话让中国记者笑了:“我能应付。”
他也不回避自己对生活的参与。在三岔,一个孩子患有血液病,需要输血。何伟认为血源不安全,但最终他没有与那里的医生争论。争执发生后,他写道:“我打车回家,一个人洗了个澡,吃了晚饭。晚上,我感到麻木。瞬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很无助。他不能有帮助,但无法呼吸。”
用连晴川的话说,“如果你想了解今天中国的真实生态,你必须有这种令人窒息的经历。”
他还在书中诚实地写下了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擦鞋的人因为他是外国人而欺负他。他们大吵了一架,差点打起来。

给他校对的美国朋友说:“我不喜欢你这样。”
然而,一位当地女孩写信给他说,这个细节让她接受并同情他,“因为我理解一个人被他曾经讨厌的东西俘获的悲伤。”
何伟并不用外国人的眼光看中国人。他用人的眼睛看人和他自己。
何伟经常被问到,“接下来中国的政治会如何变化?”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 “其实,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也不是改变中国人民。”想法。我关心的只是他们今天的想法。”然而,他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每个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剧烈地改变,反复摇摆,有时我行我素,有时又被带走。
除了一个细节之外,他很少评判这些人。
六岁的韦嘉经常感冒,父亲的反应是给他改名字。贾字有十四笔,不吉利。电脑分析显示五种元素都缺水——何伟说,“基本上我认识的中国人都缺水。”计算机给出的答案是“宋”。
改名后,孩子始终保持沉默。当大人几次问他时,他都回答“不好”。如果有什么问题,他没有给出理由或建议其他选择。与平常不同的是,他没有生气,也没有对母亲大喊大叫。他的反应只是“不”。这两句话是对自己说的。时间慢慢流逝。这种克制的态度,营造出一种无力感与一丝力量的奇怪结合。他的父亲无法理解什么是“坏”,很快就变得沮丧。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电脑曾许诺给他带来好运、巨额财富等等,但最终,这一切都是“坏事”,他无论如何都拒绝使用它。
几周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名字。
写完这个故事后,何伟写了一句有些感慨的一句话:“从今以后,他就永远叫伟嘉了。”
对此没有什么抵抗力,但他只想做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有一些尊重和感情。
前阵子,爸爸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家里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卖掉。这是一座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的清代宅邸。我在那里出生并长大直到八岁。一个人的熟悉感和稳定感就来自于此。爸爸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这房子的产权属于十几户人家,我没有财力买那房子。我只能说:“放手吧。”
放下电话,我想,就这样吧。对于一切我无法插手的事情,我只能狠心,顺其自然。只要把它想象成观看历史并在场外观看即可。我早已变了一个人,不需要这个。不要情绪化,就这样吧。
何伟的书中写道,这个家庭里,韦嘉的叔叔是一个智障聋哑人。村民们都骂他是傻子,没有人理睬他。何伟每次想跟他说话,都被村民拦住说:“他听不懂。” ”。只有6岁以下的孩子和他一起玩,他玩得很开心。有一天,韦嘉的父亲让何伟开车送一家人去镇政府。到了门口,他打开门, “政府应该每个月给我们钱来支持他。他们不给,我就把他留在这里,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傻子面无表情。
魏领着弟弟穿过院子,经过一座闪闪发光的大钢球雕塑,进了大门。
下午晚些时候,领导们开着车把群众送回山里,在离村子几公里远的地方停下来。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这么远,但他凭着本能就找到了。回家的路。
等何伟回到三岔村,傻子远远就看到他,咧着嘴笑,指着车打手势,给他讲着坐他的车下山的事。
“我明白了,”何伟说道,“我记住了。”他想要道歉,说当他明白事情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很抱歉给政府留下了一个傻瓜。但他却找不到表达歉意的方式。傻子还在兴奋地打着手势。
后来又给了补贴,给残疾人送了彩电。韦嘉的父亲把彩电送给了一个“关系”——“反正傻子也看不懂。”晚上,一个傻瓜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间里。
当孩子满六岁的时候,他就会像他父亲一样发育出桶状胸,并学会像其他人一样忽视傻瓜。
我已经学会忽略它,认为这样我就可以避免痛苦。然而,何伟却写出了我所看不起的中国,以及冷漠背后的本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灵魂的不归属,无论你意识到与否,承认与否。


阅读往期经典文章


回复以下关键词,我送你一篇周国平精彩的哲学文章
爱|爱|善|情
儿童 |家长 |父亲|女儿|教育
命运|职位|快乐|欲望|妥协|弱点
路径|生活 |沉默|真相|觉醒|尊严|使命 |本质
智慧|青年|忏悔|友谊|自然 |野心|谦虚|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