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与关西大学联合举办近代西餐文化工作坊,探讨西餐传播与受容

2021年11月18日至19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与日本关西大学开放亚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西餐、西餐、近代餐厅”研讨会在线举办。来自复旦大学、东京大学、关西大学、南开大学等研究机构的20余名中外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也吸引了数百名听众在线观看。研讨会分为五个报告。学者们围绕近代西餐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研讨会以关西大学Keiichi Uchida教授的主题演讲“西餐在现代东亚的传播和接受”为开场。内田教授首先介绍了阿儒略、利玛窦、梅杜斯等西方传教士著作中出现的西餐,以及中国人对异域风情的记载。这些记载主要出现在一些知识科普书籍中。此外,内田教授还总结了当时西餐翻译的一些对照表。由于西方文化往往来自海洋,内田教授接着介绍了清末民初上海出现的一系列西餐厅的情况以及当时的西餐文化。他用小说、杂记、广告等一系列文学材料来呈现当时的西餐。最繁华的司马路(福州路)和当时著名的西餐厅一品香。最后,内田教授介绍了《西餐之书》,该书的作者是传教士塔尔顿·佩里·克劳福德的妻子玛莎·福斯特·克劳福德。这是一本西餐食谱。内田教授对其版本和内容进行了总体介绍。除了《西式米书》之外,内田教授还介绍了《西式米书》之后紧接着出现的其他西式美食菜谱,如《西式法式菜谱》、《新中英菜谱》等。食谱”,并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异同。 。最后,他还分享了西餐食谱在日本和韩国的传播情况。内田教授的总结报告基本涵盖了后续workshop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是提纲式的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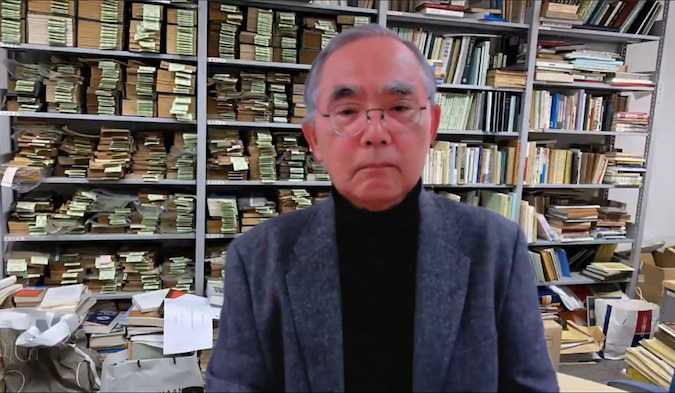
内田敬一教授
第一个报告由内田敬一教授领衔,河北师范大学戴建兵教授点评了三位报告人。
第一位发言者是上海图书馆研究员黄巍。她的报告题目是《上海图书馆中西餐食谱馆藏概况》。她主要将收集的西餐食谱分为几类,并从每一类中挑选了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具体介绍。首先,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就有专门的西餐菜谱,包括之前内田教授提到过的《西米制作书》和《西餐菜谱》。其中还发现了一本载有一些中国菜肴的书。美国红十字会中国食品食谱手册。第二类是档案中的西餐菜单,包括例如盛宣怀档案中海军营办的宴会记录、西餐请柬、溥仪的生日菜单等。第三类包括广告书籍中的西餐菜谱。来自一些食品相关工厂。第四类是一些与西餐相关的广告以及报刊上的专栏。第五类是传教杂志上的西餐教学内容。最后一类介绍西餐的历史照片。
第二位发言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黄新宇。她的演讲题目是《吃大餐:近代上海的西餐时尚,1880年代-1920年代》,主要探讨清末明初以后上海西餐文化的变迁。她总结了西餐的两种受欢迎程度。第一个出现在 1880 年代和 1890 年代。作为一种高端文化,西餐进入中国后,不得不面对中国已有的苏式宴会高端饮食文化。然而,通过将西餐融入到集餐饮和西式娱乐于一体的上海一品象酒店的推动下,西餐(大菜)——与乘坐马车、戏剧表演等四程旅游套餐相结合——晚清时期开始受到上海文化精英的欢迎。来。然而,当时的西餐并不是最高的,也不是唯一的时尚。第二波流行发生在1910-1920年代。此时的新趋势是有轨电车的普及和民用娱乐的兴起。记者选取了当时几个平民游乐场的资料来说明当时平民能吃到的西餐。当时也出现了西餐厅,如为上流社会提供的宴会餐厅和为平民游客提供的经济实惠的西餐厅。但同时也存在一种将大饭店与吸鸦片相提并论的污名化现象,后来与自由恋爱文化联系在一起。
第三场讲座由东京大学陈杰教授主讲。题目是《中国的西餐与西方礼仪》。主要介绍了曾在京都大学学校任教的服部宇吉所著的《家政学(清代家庭学校用)》一书。由他的妻子服部茂子撰写的教科书。服部茂子创办了北京最早的女子学校——玉娇女子学校。它的学生主要是社会上流社会的女性,《家政》的预期目标受众也是这类上层女性。本书试图通过提高中国妇女的教育水平,为国家的繁荣和妇女权利的维护做出贡献。本书介绍了一系列关于西餐的基础知识,主要不是具体菜谱,而是西餐的种类、鉴别、营养、饮食建议、礼仪等日常知识。它还包括许多饮料、小吃甚至冰淇淋。介绍。此外,书中还专门有一章介绍了在招待、出席或就餐时与外国人交往的适当礼仪。这是一本从日本人的角度反映当时中西文化融合的书。
在评论区,戴建兵教授补充了关于河北师范大学家政系和服部茂子及其好友秋瑾的关系的内容。
研讨会第二场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曦教授主持,陈杰教授点评。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戴建兵以正太铁路和正泰宾馆提供的西餐为切入点,利用民国时期的官方文件、报刊,探讨了正太铁路的建设和正太铁路的建设。介绍西餐、火车上的餐车餐食和当时的人 尚泰酒店西餐印象主题,放在石家庄从乡村到城市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去了解。该报告拓宽了以往针对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西方饮食文化的研究视野。这对于了解石家庄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域特色和复杂面貌也具有重要意义。陈杰教授询问了民国时期外国人在石家庄的生活情况。戴教授回答说,总体比例不低。随着铁路的修建,天主教神父和外国商人也纷纷效仿。抗战时期,日本人和朝鲜人占当地总人口的6%,还不包括驻军。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郭丽霞的报告题目是《清末民初“香槟”一词的定型过程》。报告通过对数据库、汉语教材、明清小说、词典的检索分析,删除了“香槟”一词,由于与“香槟”发音相近,我们将与“香槟”相关的翻译分为两类:“三面”报告还提到了方言在音译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匹配了“Champagne”和“Champagne”的转换。 “三边”到“香槟”随着“香槟”一词从粤语区向吴语区的转移过程,陈杰教授指出,日本似乎也存在“三边”。关于中日翻译是否存在相互影响,郭教授补充说,有必要参考陈立伟对此的讨论。
黄家轩(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研究生院研究生)以“吃青蛙的复兴:当地食俗转变中的西方因素”为题,探讨了吃青蛙的风俗是如何演变的。清末民初受到严厉批评和制裁,却在20世纪30年代再次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在这种观念转变的背后,国外食蛙习俗和养殖技术的引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吃青蛙逐渐成为一种无辜的消费行为,由此产生的支持吃青蛙的话语体系迅速取代了反对吃青蛙的传统观念,吃青蛙再次成为一种社会潮流。然而,这种“西风东传”并没有直接影响当地的饮食习俗本身(西式的青蛙烹调方式尚未被中国人接受),而是间接影响了社会心态,实现了话语的转变。系统。高曦教授询问,“吃青蛙”习俗和观念的变化是否完全是受西方影响——比如厂家的营销推广是否促进了观念的转变,以及“吃青蛙”失败的背后是否存在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的政策。对此,记者强调,虽然当时上海有一些厂家进行了宣传尝试,但力度并不大;政策的被迫改变当然也是实际控制力低等因素造成的,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西方技术和习俗的影响更为重要。

高曦教授
研讨会第三场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寰教授主持,上海图书馆史料中心黄巍点评,内田敬一教授补充发言。
洪书倩(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的主题是“咖啡文化与现代中国女性身份的建构”。她首先介绍了“咖啡”作为音译词的变化和定型过程,窥见了它被中国社会接受的过程;然后论述了国民政府号召“新生活”,积极构建以女性为核心的现代家庭关系时,“咖啡”如何成为一种新时尚。报告还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出发,指出民国报刊在讨论“咖啡馆”和“咖啡女郎”时存在“性别双重标准”,讨论现代咖啡文化中的性别差异和女性独立。有些情况。黄巍老师指出,今年年初出版的《上海咖啡地图》或许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现代咖啡文化,并强调引领咖啡潮流的传教士群体内部也存在多样性。邹振寰教授表示,“咖啡”一词也有源于澳门葡语体系的谱系。 “咖啡馆”最早的翻译也来自葡萄牙语。内田义世教授还补充说,葡汉词典中确实有“Gafei”的翻译。此外,邹教授指出,该文使用了徐克的《清百乐朝(饮食)》,其中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取自当时的期刊。最好追根溯源,进行历史批判。
苏州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王逸杰做了题为《近代上海的咖啡摊:殖民主义反思下的现代想象》的报告。它以1944年至1946年的上海咖啡摊为调查对象,探讨如何实现低价和阶级开放。它将“现代”生活方式本土化、大众化,开创了新的消费文化领域。报告还利用现代上海报纸上的广告信息,探讨了“美国货崇拜”的殖民影响以及“报纸”作为媒介构建现代生活想象的意义。还通过殖民主义理论揭示了咖啡摊的“落后”。 “评价背后隐藏的‘双重目光’困境。黄伟老师认为,文章大量使用了小报信息,值得肯定,但也可能因为小报自身的好奇心,在视角上存在局限性。另外“咖啡摊”的入口虽然新颖,但在含义上可能与“咖啡馆”的概念有重合,邹振寰教授还举了“一品香”餐厅的例子来说明,同时提供两者的餐饮场所。 “茶”和“咖啡”不仅仅是“咖啡摊”。
暨南大学研究生吴玉瑞介绍了早期南洋华文报刊的重要研究价值。他以《叻报》为主要调查对象,并参考《星报》、《每日新闻》等报刊,分析其中出现的西式饮品外来词。经过仔细整理分析,将这些外来词与《现代汉语词源》中的词条进行比对,发现一些具有海外华人特色的外来词的翻译形式可以作为最早的文献证据,填补空白。从传播情况来看,大型洋酒广告在中国早期报刊中占据显着地位,这对研究南阳地区的社会生活史具有重要意义。黄伟老师希望通过翻译和介绍了解南阳地区与大陆的联系。邹振寰教授补充说,当时南洋出版了很多语文教材,在抗战时期影响很大,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对于报告中使用的词源词典版本,邹教授认为,应尽可能参考最新版本,以掌握最前沿的学术信息。内田芳世教授补充说,对于“啤酒”的翻译,可以参考1883年(光绪九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华谊通语》一书。

邹振寰教授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生赵惠斌做了题为“饮食困境:营养科学在现代中国社会的遭遇”的报告。他从知识和学科转型的角度分析了晚清以来营养科学传入中国的情况。过程中,探讨了中国传统知识观念在面对“西学”冲击时的交互过程: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建立“科学”话语;另一方面,传统饮食理念的创新与重构面临多重挑战限制。在此背景下,家政教科书的变化、烹饪方法的改进、“素食与肉类”的争论等话题变得更加丰富。邹振寰教授指出,有关营养的讨论中经常出现的“养生”、“戒杀”等概念,可能并不完全源于佛教体系。比如杀牛杀狗的价值观变化,其实更多的是与19世纪的西方传统有关。随之而来的想法纠缠在一起。

第四场由南开大学文学院郭丽霞教授主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李启耀点评。
朱峰(日本京都圣母女子大学教授)主要以《西方法国食谱》为中心,探讨传教士翻译中的西方饮食文化。他从版本、广告和书中的中文翻译三个角度考察了该书的出版情况。产生了社会反响和深远影响,表达了译者面对外来文化的中国化的同情和理解。报道还提到《来客须知》、《西方问答》、《外国美食制作书》等文字是中国记载中了解西方饮食文化的重要资料。郭丽霞教授询问《西药方》为何有大量“音译”。朱峰教授认为,主要是因为当时汉语没有合适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些概念。当中文有对应词时,大多是直译。 。对于音译对应的汉字,朱教授认为,翻译主要是根据上海话的发音。不过,由于19世纪和今天的发音存在差异,仍然需要仔细比较。
谢毅(意大利佩斯卡拉邓南遮大学U d'A语言中心中文教师)主要介绍了意大利烹饪文化和传统食谱中不可替代的“三剑客”——罗勒、迷迭香和百里香。通过比较这三种香料在西方和中国的接受历史和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这些草药在中国历史上主要用作药材而不是作为膳食成分,并且与中国传统食品密切相关文化。内田义世教授指出,意大利学术界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神农百草经》,在研究中也可以参考这部著作。李启耀老师强调,物质文化史不仅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出版界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最近出版的《沙漠与餐桌:丝路美食的起源》一书也与这个话题密切相关。
陈丽英(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研究生)以“新京”(即长春)的“中央饭店”为例,探讨伪满洲国的城市阶级与文化消费。报告希望为“日常生活史”视角下的伪满洲国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通过对《新京》的城市空间、物价、消费水平以及具体文本《鲜丽标》的分析,展示了城市作为消费空间“中心饭店”及其背后隐藏的城市阶层和文化消费分化。报告还从宏观到微观将东北地区饮食习惯的剧变与殖民权力的投射联系起来,探讨了极具象征意义的日常饮食所体现的殖民再生产等相关问题。李启耀老师认为,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视角是对前人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补充,但研究综述部分在梳理日本学界和欧美学界的成果方面稍显不足。可以参考月泽明的《伪满洲国首都规划》一书。另外,关于中央饭店的文献,《贤力表》一书当然非常重要,反映顾客印象的材料也应该纳入调查范围。
杨歌(澳门科技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以“花筑老哈菜”为例,探讨现代“西风东来”的影响及国际城市对哈尔滨地方美食风格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报告指出,近代以来,哈尔滨“中西合璧”的城市形态促成了中俄乃至中西饮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最终的“花筑老哈菜”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实现了“花筑老哈菜”的转型。从“色深、汁浓、味浓”到“油光、滑嫩、酥脆”的转变。郭丽霞教授想知道“花竹老哈菜”的案例是否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记者回应称,东传西传的影响确实不限于本案,但各种变化的特点在本案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显然,因此是围绕它展开的,未来还可以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
11月19日的报告由陈杰教授主持,高曦教授点评。
第一位演讲者是日本爱知大学的 Masazumi Shioyama 教授。他的演讲题目是“中国人如何表达西餐的烹饪方法——窥探现代西方人的外来文化翻译”。之前很多研究都说《朝阳翻书》使用的是普通话,但燕山教授试图论证这种“普通话”或“白话普通话”的具体特征。首先,虚词的出现频率符合白话普通话的习惯。随后,采用了约瑟夫·阿约斯的研究结论,从动词独立性(需要添加补足语来完成对一个动作的描述)的角度讨论了《朝阳翻书》中白话普通话的特点。紧接着,燕山教授就进入了补语的讨论。大量的补语也体现了白话普通话的语言特点。最后是关于助词和量词的内容。 “了”、“就”等助词和量词的大量使用,也体现了《朝阳翻书》的口语语言特征。陈杰教授和燕山教授讨论了《洋食记》中白话普通话语言特征的出现是否与西餐的特殊要求有关。他们认为本来中国白话就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但由于书写都是文言文,而文言文无法准确表达西餐的过程,所以西餐的传入促使这种白话文被记录为文学菜谱。
第二位发言者是大阪大学野村忠雄教授。他的报告题为《咖喱中文名简史》,重点介绍了咖喱的翻译。正如一开始提到的,虽然咖喱原本是印度菜系,但由于是从英国传入的,所以当时普遍被视为西餐。译词通常是先音译,再翻译成意译,但咖喱则相反。最早被译为意译,19世纪上半叶被译为“姜黄”。所谓姜黄,现在称为“姜黄”,是用来制作咖喱的。原料之一,又因为喜欢黄咖喱的英国人将这种着色原料视为咖喱最具代表性的材料,所以选择了只是原料之一的姜黄作为咖喱的译名。但到了19世纪中叶,广东出现了“家丽”、“家丽”等译词,一般源自粤语。到了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今天所用的翻译词“咖喱”。但各种译本基本上可以互换使用。田之村教授推测,这种从意译到音译的转变,可能是由于中国人对西餐的了解增加,发现姜黄只是咖喱的原料之一,所以改变了翻译。
进入下半场,来自关西大学的杨一鸣首先带来了《现代西餐食谱考察》。杨一鸣首先介绍了外文原著《西法食谱》的写作过程、译者、上海领事易孟实的夫人以及易孟实本人的生活经历。其中,或许是出于中文使用的考虑,原著《东方烹饪书》的翻译存在一定的删除,插图也被删除。随后,记者介绍了《西式法国菜谱》的一些翻译特点,如计量单位的转换、食材、菜名甚至动词的音译、上海方言对翻译的影响等。
最后的报告是孙浩(昆明理工大学)的《现代报纸空间中的西餐文学研究》。主要利用国家报刊索引数据库检索面包相关文献。记者提到,面包刚传入中国时,常被译为馒头。克鲁泡特金的《面包拿》等文献被翻译传入中国后,李大钊等人逐渐将面包与政治联系起来,用面包来指代人们的吃饭权。然后提到面包在文学中被作为与爱情有关的意象,并提到人们对面包作为娱乐膳食的文化印象。紧接着,记者提到,20世纪以来,一些以吃西餐作为崇拜外国人的观念逐渐出现,甚至把对西餐的敌意延伸到西餐餐具、刀叉上。
两场报告结束后,高曦教授对“面包馒头”的几种翻译以及西方食谱中的营养概念提出了质疑。对此,杨一鸣提到了金一平的一篇文章,认为面包这个词的翻译应该来自澳门,以后应该逐渐推广。 《西餐食谱》的中译本没有太多营养概念的内容,而英文版却有很多。陈杰老师补充说,服部重子曾经提到过葡萄酒的营养价值。




